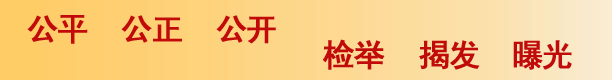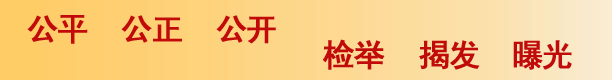我对科普由爱好到认识它是一种责任,开始于1958年作大学教师。当时一种朴素的想法是,要作一名好教师,需要能够用浅显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说清楚,而科普著作最重要的特点正是这样。所以为了作一名合格的教师,就需要浏览和阅读大量的科普著作,从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教学。
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在教学大致能够应付局面以后。逐渐产生了一种科普创作的冲动,也想写一点科普文章。退休以后,教学与科研的压力都没有了,于是便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普写作中去。迄今已经写作了有关科普的文章百余篇,出版过三本科普文集(《拉家常说力学》、《力学史杂谈》、《音乐中的科学》),还有三本在出版中。还担任了《大众力学丛书》的主编,该丛书由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了十三本,还有五本在编辑中。
几十年对科普著作阅读、写作的经历,逐渐对所谓科普有了新的体会和感受。从原来模模糊糊的认识逐渐清晰了起来。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些感受;
第一,科普是高水平的事业。
在初接触科普读物时,有一种错觉,似乎科普并不要求很高的学术水平。我国的学术界也有一种不成文的看法。似乎科普文章水平低。所以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计算研究成果时,不算数。这就是刊物一直缺少优秀的科普文章来源的根本原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获得1971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噶波(Dennis Gabor,1900-1979)是由于1948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种新的显微原理》(A newmicroscopic principle)的通俗文章揭示了全息照相的原理。伽利略1638年出版的通俗读物《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是一本不朽的科学巨著。薛定谔的科普读物《什么是生命》不仅从物理学的角度开创性地解释生命现象,并且预言了遗传基因的物质基础,为DNA的发现吹响了前奏。
可见,科普作品也可以登堂入室达到科学殿堂最高水平。其实,它更多地反映出一种科学家的文风问题。同样的科学研究成果,是用为更多的大众易于接受的语言来介绍,还是用深奥难懂的语言来介绍。效果是很不同的。作为科学工作者,特别从事科学教育的教师,必须学会使用通俗的语言来介绍自己的成果。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学界有一段顺口溜,说是“深入浅出是通俗,浅入浅出是庸俗,深入深出尚犹可,浅入深出最可恶。”是的,我们应当追求深入浅出,把深奥的科学道理讲得易于接受。而那些把本来很容易懂的问题讲得深奥难懂,乃至把空洞无物的事情说得玄玄乎乎,这就是爱因斯坦说的:“在我看来,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被称为科普读物的书都是要吓唬读者,(’真吓人!’’我们进步得好快!’等等。)而不是向读者清楚明白、深入浅出地介绍基本的目的和方法。” 这实在是很可恶的。
第二,上面这种误解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认为科普很容易。
我自己就有深切的体会。我平时还是爱看科普作品的,可一到自己拿起笔来,却才真正体会到它的难处。它比我以前习惯写的那种“科研八股”要难多了,就会发现,不是知识不够,就是文字表达的笔力太弱。实际做起来可是不容易。
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德国生物学家汤姆森(J.A.Thomson,1861-1933)所著的通俗读物《科学大纲》时,王云五对该书所写的序言的开头两段是:
“今人之一言及科学,则以为浩瀚广漠,不知纪极,或畏其艰深幽眇,望而却步。故愈钻颂科学之神妙瑰奇,而科学之去人愈远。格列高里(Gregory)分智识界为两类:一为创造智识之人,一为传布智识之人。今日科学智识造诣愈深;而人之去科学之隔阂愈甚,则传布智识者之过耳。
夫传布科学,似易而实难。一,传布者非自身亦为创造之科学家,则不足以既其深。二,传布者非掩贯众科之科学家,则不足既其广。二者具矣,而无善譬曲喻引人入胜之文字,仍未足尽传布之能事。此所以迟之又久,求一取材广博,叙述浅显之科学成书而终未见也。乃距今不数月前,竟有汤姆生(J.A.Thomson)教授主撰之《科学大纲》赫然出现;是殆足弥缝学界之缺憾,而为科学前途贺乎。”
这段话很生动地说明科普的重要性和它的难度。要做好科学的传播,一要自己有科学研究的深度,二要有对科学知识的广度,还要有能够引人入胜的文字表达能力。
就拿我自己写科普文章的过程来说,许多日常见惯的事物,其科学道理并不是都透彻了解的。普通的研究者也很少提及。所以先得把这些现象背后的道理吃透。写《捞面条的学问》就得自己不断从捞面条中摸透二次流的规律。写倒啤酒,我平时虽然很少喝酒,自己还是买了几瓶啤酒,从头实验啤酒冒泡的行为,并做出科学解释。为了写飞去来器,自己不知做过多少飞去来器,直到能够自由地扔出去飞回来才心里有底。要写笛子,我自己又动手制作了许多尺寸不同、音调不同的笛子。直到总结出一个计算音调与开孔长度和内径的关系的近似公式为止。这还不算,还要收集用同一原理能够解释的各种事物。所以实际上,好的科普是要从头做研究的。
有些事情需要查它的出处,就要查阅原始文献。特别是古代文献,不好查。我写《人类是怎样学会量血压的》就要查伯努利和泊萧叶关于流体力学的原始文献。这种文献在现在我们的图书馆里很难找到,在网上有时可以查到一点,有时还得托人到国外去找。记得我在写一篇《从腐草化萤说起》的科普文章,为了找到我国历史上最早认为萤是产卵在草中的一位学者,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起先是在明末方以智的类书《通雅》中,查到号“合溪”的认为“萤产草中”,但不知合溪为何许人也,询问文科的教授,一般也回答不出。一直到最后在一本新出的历代名人别号词典中才查到原来合溪就是南宋的戴侗,最后才在他著的《六书故》中找到他的原始说法。前后经过了十多年。
出处和科学性都具备的条件下,是可以动笔写了,不过在我以前写惯了“科研八股”,第一次写出来,还是有八股味,总得反复修改若干次,有时还要发出去听听同行们的意见,再修改一遍才脱手。
总之,写一篇真正属于原创的科普文章,比以前写一篇科研论文,花的时间要多多了。我想,它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是一种要求更透彻的研究和创新。写过几篇以后,还是对它有了兴趣。虽然同仁们有时开玩笑说是“不务正业”。自己也乐此不疲。
第三,猎奇不是科普。
目前,主持主流媒体的大腕特别是视频节目的主持人多是新闻专业出身。由于他们有一种职业的判断,“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加以有的出版单位和作者,单纯认为科普需要尽量吸引人们的眼球。读者多了自然就“普”了。所以许多媒体把科普栏目办成了“猎奇”。什么尼斯湖怪兽、神农架野人、三条腿鸡、五条腿羊,“喝尿保健”和“对打呼噜者的侦探”,什么神奇说什么。固然,其中也介绍过不少科技方面的新闻。不过科技新闻和科学普及又不能看作是一回事。至于“猎奇”则和科学普及根本是两码事。
那么,什么是科学普及呢?我认为科学普及是对公众的科学知识教育。所以科普不能看作新闻而应当看作“教育”。教育行业选择内容的标准,不是什么新奇选什么,而是什么重要选什么。也就是以什么知识会对受众以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作为选材的标准。用教育的标准来选取科学普及的选题,应当选取那些对公众生活和认识影响较大的论题作为科学普及的论题,而不是以新奇作为选题标准。
科学普及是一种教育,但它又不同于学校教育。学校教育面对的是一群年龄和经历大致相同的受教育者来进行的。所以可以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集中进行授课的方式。而科普是社会对公众进行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科普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群众。他们的年龄是从青少年到老年,他们的经历不同,有文盲也有大知识分子,还有科学家,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百姓。如果把科普办成了课堂搬家,那便会彻底失败。
当然对大众解释重要的科学知识,是科普。如果能够通过介绍这些科学知识,吸引人们进一步思考,进入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使他们成为新的科学家,这样的科普书籍就更值得珍贵。薛定谔的《什么是生命》和法国佛罗马利翁的《大众天文学》就属于这样的高水平的科普。前一本引导一部分年轻人探求遗传物质,成为DNA的发现者,后一本培养出了若干有名的天文学家。就是说,科普不只限于把常见现象的科学道理说清楚,更重要的是由此出发把读者引向更深入的思考。我写《捞面条的学问》就是想学习那些好的科普著作,把用筷子捞面条的常识讲完后,进一步提出“分离技术”的问题,然后进一步介绍核工程中重要的技术关键铀的同位素的分离问题。
随便在“百度”搜素引擎上输入一个“科学算命”词,就可以搜索出上千万的网页,这种迷信的广泛说明,我们的科普任重而道远。科普应当是我们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我们的国情在鞭策我们要成为好的科普作者,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锻炼自己,不断研究,自己首先要成为对研究问题具有浓厚兴趣的人,要不断积累各方面的知识,积累丰富的资料,还要磨练自己的表达能力,并且要选取对大众重要的科学知识作为写作的内容。这些,就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体会,是一个不断向往的努力方向。
201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