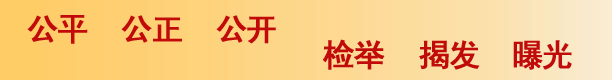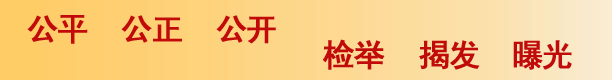2014年2月14号,元宵节和情人节,收到编辑邮件说我们挑战上新世永久厄尔尼诺的文章作为Science的Report接受了。确实很开心,觉得这不辜负在巴塞罗那时别人都在海边游泳喝酒我把自己关在宾馆里写文章,也不辜负了许多个凌晨1,2点钟还在和老板互发邮件一遍一遍修改论文的不眠夜。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留作纪念并且或许对一些朋友们有参考意义。
当初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只想着在时间尺度上把前人的工作进行延伸。没想到结果出来了以后,根本就不支持永久厄尔尼诺的观点。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永久厄尔尼诺作为一个古气候领域的假设,从2002年左右气候模型预计了它的存在,到2005年海水温度重建的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这十几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仅我们系的一位大拿A教授就这个观点在Nature, Science上发表了4-5篇文章。原来设想的与他的合作是不可能了。这个结果的发表就意味着给自己树立一大堆敌人。老板却毫不在乎。他不羁的性格在年轻时曾经得罪过本领域的大鳄,曾经被威胁在这个圈子里根本混不下去。他却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还生存的不错。但我却不知道我是否有会这样的好运。
2013年9月10号,英国布里斯托,上新世大会。老板没来,我来了。我心想,就当是关云长单刀赴会吧。我被安排在第一天的下午做报告。在我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报告都是讲永久厄尔尼诺的。而我的分会主席,正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提出者B教授。我硬着头皮上去,心想与其不痛不痒的说几句,还不如把话挑明了。于是我的开场白大概如下“大家好,我报告的题目很长,说了一大堆。但是其实总结起来,就是挑战永久厄尔尼诺的观点。我意识到在我之前有XYZ做了报告,在我之后还有XYZ要做报告。但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台下笑声)。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结果以及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并且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还好,报告过程中全场笑了好几次。没有预想中的尴尬。会议休息期间,很多人上来和我理论。B教授比较有风度,提出了几个意见还算中肯。可是他手下的兵将就并非如此。C,D等人毕业于B的实验室,但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PI了。C把这件事搞的类似个人恩怨,每次都要纠集几个人上来跟我吵。我最后跟他说,我喜欢你的批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让我考虑的更加周全,让我的科学做的更好。同样的,我对你们之前的结果的批评,希望你也能用同样的心态来对待。话我说了,是否能听进去就不知道。
2013年9月18号,我第一次把和老板反反复复改过7个版本的稿件投到了Science。Science的网站上说,80%的投稿是不送审的。一般7-10天内就会有回音。我们等了三周,还没有消息。发信问编辑,编辑说已经邀请人审稿了,等第一个人接受审稿邀请之后,就会给我们发邮件确认。还好,我们是那20%了。五个星期以后,审稿意见回来了。共有四个审稿人。三个人都支持修改后发表,第四个人态度比较消极,提了不少意见。编辑说三个星期内改回。那就改吧。期间遇到AGU年会,要准备报告还要开会,于是跟编辑说推迟两个星期交稿。编辑说没问题。在AGU年会的时候,老板的特邀报告讲了我们的这项结果(因为我讲了另一个更新的工作)。效果非常好。老板的那一套性格,面对几百个听众就跟面对几个自己最好的哥们似的,那么放松那么嬉笑自若,别人是很难学得来的。但让人惊讶的是,B教授的报告里,竟然全变调了。他不再攻击我们的数据有问题,而是花了所有的时间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结果和他们之前的数据并没有什么两样。听完他的报告,有人提问有关数据的问题。可是我却没有留下来听这些细节的纠缠。我心想,我得赶紧回去继续修改我的论文。等它在Science发表的时候,比花100个小时和你们辩论这些细节有意义多了。于是我在旧金山连吃了两天的麦当劳快餐,就为了能赶回宾馆修改文章。很巧的是这一次,我和老板又改了7个版本。投回。
又花了近五个星期,审稿意见回来了。这次送了原来四个审稿人中的三个。两个人基本没有意见了,可是第三个人的态度转变了。基本上就是说应该据掉我们的文章。而他的论点竟然与B教授的新论点一样,我们的结论和他们数据没什么区别。编辑又让我们三个星期内改回。我很生气,老板却安慰我,说他之前的N/S文章有最多让他改四遍的。每发一篇N/S,他就感觉褪一层皮。我笑了,说之前只知道你文章多,不知道你受过这么多煎熬。改吧。我们又认真就每一个审稿意见进行了回复。最后,老板写了给编辑的Cover Letter,里面说我们认真考虑回复了每一个审稿意见。但我们觉得不能说服审稿人3了。但是,我们的数据与之前永久厄尔尼诺的观点的确是不一致的,因为1,2,3,4条。最后一句说,我们期待你的决定。
一个星期后,文章接受了。我们成为了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