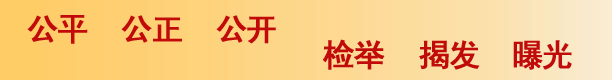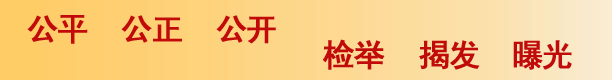写毕业论文之前,设想过自己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障碍,比如拖延症复发、资料不够、脑力不够等等。等到真正处于这一过程之中,才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一旦有了明确的截止日期,那么拖延症会自动转换为强迫症,连作梦都梦见自己对着电脑写写算算,并且旁边的倒计时显示屏还在滴滴闪烁;资料就更不是问题了,只要愿意找,总会找到比想象中更多、更好用的文献,以至于以前很多看起来不错的存货只能暂时搁置到“剩余资料”中,实在觉得对不起它们;脑力不够,好像也不是问题,因为到最后发现体力更重要。
我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自我认同感太低”,时常怀疑自己的价值。比如有一次看到某篇博士论文。她与我关注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是她是以数理的方式来处理,具体而言,是综合了营养学、生态学、农业经济管理。她在论文中列举的大量图表、数据、公式;又看到她在论文后列出的她主持和参加的共计20项国开行或农业部的课题、项目。这样一比,顿时感觉自己的博士论文弱爆了,因为是以文字为主,数据很少。
虽然在面对实际的社会问题时,我很早就发现,单靠图表和数据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且选择转行。然而,由于本科与研究生阶段都是接受理工科教育,因此对于数据仍抱有一种近乎教徒般的原始崇拜。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我考上历史专业后,也是将要离开版纳的日子,几位老友在一个ktv聚会。一位师兄问我,这个专业难不难考。我懒得多言,所以就回答说“还好”。然后他说,是不是这种文科专业只要报了就能够考上?当时我忽然感到一股凉意。其实这位师兄一直对我很好,他的妻子也时常看我的博客,偶尔会赞美几句……但是那一刻我才知,在大家心目中,文科其实还是比理工科弱很多的。后来我想,也许他并不是对文科有轻视,而是我自己太敏感了。
接下来,在文科的环境中侵染了三年,我以为自己内心中对于“文字”与“数字”的等级观念已经消失了。但是直到看到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我才发现,根本没有。思绪纷乱……幸好,连日写论文,已经形成机械般的节奏,过了一会儿仍旧继续看文献、写论文。直到某一天,心里的结忽然解开了。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那篇论文的大意是,我们的农业是缺乏主导性的农业,即市场需要什么,农业就提供什么;市场需要多少,农业就提供多少。在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低下的时候,这种模式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农产品产量逐年上升”绝对是普大喜奔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变得复杂了,农业管理者面临着更多精细的权衡——产量提高的价值是否能弥补治污的价值?从每日消费量来看,2009年城市居民膳食的肉类摄入量已经超过营养目标上限37g,而这个数字仍旧继续增加。过量的肉食消费为资源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那篇论文提出的观点是:基于营养目标的肉食需求要比非营养目标的肉类需求每年节约饲料粮食若干;节约水源若干亿吨(这个数字还未包括牲畜粪便污染的水资源和屠宰、加工等环节使用的水资源);节约耕地面积若干公顷,等等等等。(作者主要是从生态的角度考虑,而如果从医疗的角度考虑,那么基于营养目标的肉食需求量比非营养目标的肉类需求每年节约公费医疗对于慢性病的投入有多少?这样一算估计就更有说服力了。)
这是一篇不错的论文。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基于营养目标”来生产和消费肉食?对于这一问题的两个关键群体——生产者和消费者——大概都缺乏直接动力作出这样的选择。对于肉食生产者来说,自然希望人家消费的肉食越多越好;而消费者呢?从营养学文献看,在90年代就有学者提倡控制肉食消费量,但是现实情况则完全相反,中国疾控中心营养食品所翟凤英(2007)对同一样本人群的食物消费、营养状况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五次追踪研究,应用11年资料分析发现,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量增加,成年居民牲畜肉类的消费平均每天增加了50-60g。
也就是说,尽管从理论上而言,“基于营养目标”来生产和消费肉食是个不错的提议。但是从实际上而言,这里面还存在着诸多障碍。事实上,从民国时期开始,就有人从营养和生态的角度来提倡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其声势之浩大甚至更胜于今日。但是这个提议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就是我在论文中研究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何今天的营养学家的建议那么软弱无力。而这个问题,是不能光靠数字来回答的。这样一想,我觉得自己的研究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了。“自我认同”感又得到恢复了。
当然,心理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所以,看到另外一篇论文,我的“自我认同感”又降至冰点。那篇论文一共有280页,“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大概可以够十个博士毕业,论文和书评一共有14篇(其中有8篇是c刊或者c刊扩展版),还出版了一本学术译作。他的博士论文,材料组织方式与观点的陈述语气都极为老练,几乎完全摆脱了学生味道,而这种功力,显然是与长期对某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巨大的阅读量分不开的。
而对于我来说,这两样都是硬伤。首先,进入历史这一学科的时间太短。其次,因为偏爱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而很多问题,往往并不是某一学科能给予完美解释的,所以我在研究中往往会牵涉到其他学科。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支撑,尤其是史学功底还未打得很扎实的时候,这种“跨界”研究很容易流于肤浅。而且对于短短的三年学制的博士生来说,轻易尝试“跨界”还有一个风险——你写的论文可能会难以得到任何一个学术圈的认同,从而影响论文的发表以及找工作。当然,特别有天赋者例外。
上个月我参加了本所的研究生学术报告会,我报告后,除了指定的评委老师提出问题之外,其他老师并没有一位提出问题,而对于其他学生的报告,他们的讨论还是颇踊跃的——显然,他们对我的研究不感兴趣;又或者感觉我的报告水平太差,没有讨论的价值。当时真是感觉寂寞而自卑。我忽然觉得自己跨专业、跨学科研究的经历很失败。现在过了一个多月,我对毕业论文又进行了一些修改,感觉有所改进——但还是没有达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在答辩时让评委老师满意。
但是在某一天的某一刻,我忽然也想通了——我与以往的自己、那个跳跃性地选择专业与职业的自己和解了。
一路走来,很容易看到:那些对专业忠诚度高、对学校或者单位忠诚度高的人,基本上比那些频繁换专业、换单位的人过得更顺利。比如我本科同一级的一位女生,毕业后就留校工作,然后读了本校的研究生,现在她已经当上我们那个学院的副院长了;又比如,本科同宿舍的舍友,毕业后从事外贸工作,前几年她自己开了公司,而她研究生毕业的老公,也在工作几年后选择辞职和她一起干;又比如,同一届的研究生舍友,毕业后就一直没有换工作的,也纷纷完成了人生大事,生娃买房评职称;又比如,一起读博士的人,如果是从硕士阶段就从事和博士一样的专业,那么在人脉积累、知识基础方面,明显比跨专业报考的学生具有更大的优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么,如果可以从头选择,我是否就会对某个专业或者某个单位、某个学校“从一而终”吗?
不会。至今还记得大三时,因为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以地养地 浑善达克草逼沙退》一篇报告,而对“恢复生态学”专业产生兴趣。又因为一直对云南的神秘和美好充满向往,所以我选择了版纳植物园的生态学专业。但是后来发现,“生态学”与“解决实际生态问题”是两回事。研究生快毕业时,导师有一次问我想不想继续读博?我说不想。其实一直很舍不得离开云南,但是一想到,如果读博,我只不过是继续在哀牢山上拉拉样方、在电脑前分析数据阅读文献、然而当我作这些事情的时候,哀牢山下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采矿。而版纳的热带雨林也仍在继续被砍伐、被橡胶林占据……
本来以为自己不会再继续读博,但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最终还是读了,跨专业报考了农学史。其实不同的专业,本质区别在于解释世界的方式不同,关注点亦不同。所以选择一个专业,意味着选择了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相比较以前,我喜欢现在这种方式。但是如果没有之前的经历,也很难体会现在这种解释方式的好。因此,如果重来一遍,或许还是会是这样的经过。
前阵子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本来是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就在博士快要毕业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于是退学,去考环境法学,并且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虽然他考了几次没有考上,但是与他聊天时,我能感觉到他对于自己所选专业的喜爱与认同感。对于这样的人,我很佩服——并不是因为我觉得环境法学比其他学科更有意义,其实到现在,我不再觉得某个专业比另外的专业更有意义或者更没有意义。而是因为,一个人找到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哪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压抑自己的内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最近看到一句话,“什么是我心里那股乱窜、让我深感不安却无法操控的能量?我是否倾听到了它的需要,我是否学会掌控它来为人类造福了?……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不同,臣服于自己的命运,像大禹治水一样,把内心奔突莽撞的那股能量疏导利用,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一个人的心,藏着多少连自己都不知晓的隐疾。某些事件,就像一把手术刀,不动声色地把那些秘密呈现在你眼前。于是你不得不主动寻找治疗方案,全力抢救,起死回生。而窗外,一直是人间四月天,阳光晴好,柳絮纷飞,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